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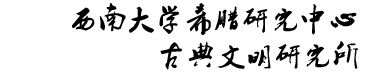
| 哈德良:不倦的旅人 |
| (发布日期: 2016-03-03 15:26:44 阅读:次) |
宋立宏
animula vagula blandula, hospes comesque corporis, quo nunc abibis? in loca pallidularigida nubila – nec ut soles dabis iocos.
小魂灵,小游荡的,小可爱, 肉体的访客和侣伴, 你如今要前往何方?那地 苍白、荒凉、昏暗—— 你也开不了往日的玩笑。
在过去几十年中,罗马皇帝的学术传记不断涌现。迄今为止,前期罗马帝国的重要皇帝都有了传记,奥古斯都、尼禄、卡里古拉等著名皇帝的传记甚至不下五六部。这一现象在方今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大潮中不啻为逆流,其出现颇有助于我们咀嚼历史的耐人寻味之处。罗马帝国的所有文献是贵族写给贵族看的,下层人民不具备阅读它们的能力、闲暇或品味。古典历史学家对此了然于心,塔西佗从不会用《新约》的口气谈论奴仆和渔夫,阿米亚努斯·马尔凯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甚至为自己把笔墨浪费在下层人民身上而向读者道歉。古今对照之下,便出现了吊诡:古代盛行直接民主,精英胜流却对芸芸众生不屑一顾;而今高倡间接民主,他们反倒对大众文化津津乐道。那些坚持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不过是按照史料能反映出的历史行事罢了。但由于是逆流而动,自然容易招致非议。弗格斯·米勒对当代罗马史研究影响重大,他对帝王传记作为一种体裁的质疑颇为中肯,而且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至少需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才有可能去写一部帝王传记:要么这位皇帝是“真正的革新者”,要么“有足够多的直接来自他的材料”。[1] 换言之,前一个条件是说值不值得写,后一个条件是说写不写得出来。 哈德良无疑是值得写的。他甫一登基便从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撤兵,不久又在日耳曼、不列颠和北非建造人工边界(limes),这些举措宣告帝国过度扩张的时代从此结束,罗马史上最强盛、最安宁的一段时日由此肇始。然而,哈德良传能否令人满意地写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那么肯定了。 哈德良在位时间为公元117至138年。今人了解公元117到284年间罗马史的惟一详实的古代文献是《奥古斯都史》(Historia Augusta)。这是一部迷宫般的托名之作,自赫尔曼·德绍(Hermann Dessau)于1889年发表文章以来,几代学者围绕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作伪动机展开了激烈争论,至今歧说纷纭。安东尼·伯利在其近著《哈德良:躁动不安的皇帝》中倾向于认可目前占据主流的观点,即成书于4世纪末(第4页)。除此之外,尚有3世纪初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的《罗马史》,但有关哈德良的部分(卷69)只保留在拜占庭时期所做的摘要中。有没有直接来自哈德良的史料呢?有,但屈指可数。哈德良喜欢舞文弄墨,甚至写过一部书信体自传,[2] 可最终只有几首短诗传世,其中最著名者正是本文开篇所引的临终绝笔。另外,几条铭文记载了他发表的演讲,若干法律条文保留了他对法律疑问的批复。 尽管史料残缺空白之处所在多有,但伯利仍然贡献出一本长达400页(正文307页)的传记。读后让人感到,史料的局限似乎并未妨碍作者完整而匀称地再现出哈德良的一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者娴熟运用了大量铭文、钱币和纸草,其中有些是上世纪中叶以后新发现的,譬如写到哈德良长城时使用了雯都兰达(Vindolanda)木牍文书(第134页以次),写到犹太人叛乱时使用了巴尔·科赫巴的纸草书信(第269页以次)。[3] 要想把这些零碎断烂的材料拼合连缀成条理井然的叙事,绝非易事。不过伯利做得极为出色,尤其在利用它们考证相关年代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作者还明确界说了根据史料所做的推测乃至猜测的部分,从而使哈德良的生平行止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这堪称此书取得的一大成就。 全书除引言后记之外共21章,可分为两部分。前7章致力于重构哈德良41岁登基前的事迹。哈德良虽然生于罗马,但即位前已有大半时间逗留在意大利之外,故相关直接记载甚为稀少,伯利在这部分主要利用了小普林尼的著作,后者的书信和颂辞多次提及哈德良的亲戚朋友。后14章细致考察了哈德良的统治,系全书重点所在。哈德良在位期间(共21年)两度长途旅行,足迹几乎遍及帝国各地,在环地中海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城市中,今天仍可看见纪念他到访的建筑或铭文。因此,他在位期间有一半以上时间不在罗马城,这是他异于其他罗马皇帝最明显之处,也是本书副标题“躁动不安”(restless)一词的明指。故后14章基本按照他在行省中的巡行路线组织起来。古代作家普遍认为,哈德良之所以嗜好旅行,能爬上叙利亚的山顶观看日出,并沿着尼罗河探访古迹,乃是受其不知餍足的好奇心驱动。但伯利的考察表明,这不仅仅是个人兴趣的反映,也是管理帝国的一种方法。哈德良可以借机视察边防、整饬军纪、确保军队忠诚,同时又可以督察地方官员的业绩,以决定他们日后的升迁。更重要的是,此举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沟通的重要途径,哈德良往往及时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通过财政资助、兴修土木等形式满足臣民的要求。说到底,巡行帝国各地是哈德良革新行省管理的重要措施。 伯利虽然按时间顺序编排全书,但书中有两个主题反复出现,它们体现了作者对哈德良的公共形象的理解。一方面,伯利把哈德良塑造成一个“新的奥古斯都”,指出哈德良希望臣民将他视为第二位奥古斯都,故在许多方面刻意模仿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大至放弃领土扩张,改革军队;小至佩带刻有奥古斯都头像的图章戒指,在钱币上使用让人联想起奥古斯都的姓名,乃至迟迟不肯接受“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等(第96、108、111、118、147、200、203、215、296页)。哈德良努力经营这一公共形象,显然是为了强调他对政治传统的继承。这里或许值得注意但被本书忽略的另一处联系是哈德良的建筑活动。在所有罗马皇帝中,哈德良恐怕最能洞察建筑对公众心理的影响。他统治期间热衷于资助各种纪念性建筑的修建,流传至今的此类建筑是罗马帝国最经久的物质遗产,不仅在当时为各行省打上了“罗马”的印记,还塑造了后人对“帝国”的想象。哈德良在这方面可能也以奥古斯都为榜样,因为除了奥古斯都,只有他才对帝国全境的城市投入了如此多的私人关注。[4] 以罗马为例,奥古斯都改造罗马后,曾夸耀自己发现的是座砖坯之城,而交付的是座大理石之都。罗马城内的万神殿(Pantheon)最初由奥古斯都的将军兼女婿阿格里帕为皇室所建,后遭焚毁。今日游客所见的万神殿,其实是哈德良大约在118-125年间重建的,但哈德良没有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其上,而仍沿用最初的题铭: M·AGRIPPA·L·F·COS·TERTIVM·FECIT (路奇乌斯之子、三次出任执政官的马尔库斯·阿格里帕修建) 这未尝没有在公共领域内维持政治传统连续性的考虑。 另一方面,伯利突出强调了哈德良是一位希腊文化爱好者。他自幼喜读希腊文学,以致获得带有鹦鹉学舌之义的绰号“小希腊人”(Graeculus)。成年后出任雅典的执政官。登基后对希腊文化的崇敬愈发不可收拾,甚至亲自出席了位于厄琉西斯(Eleusis)的秘仪,此地距离雅典城西北十八公里,每年举办全希腊影响最大的秘密祭典,庆祝谷物女神德墨忒尔将其女儿救出冥府,以此祈盼美好的来世;哈德良是奥古斯都之后第二位参加这一秘仪的罗马皇帝。皇帝的喜好必然影响他的决策。他像伯里克利那样把雅典建设成希腊世界的中心;他觉得犹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实在与希腊世界格格不入,遂想把耶路撒冷改造成希腊城市,并下令严禁割礼,这可能引发了他在位期间最严重的一次叛乱,犹太人后来一提到他的名字,总不忘在后面加上犹太教最刻毒的祝祷——“愿他的尸骨被碾作尘”。伯利把希腊人对他的赞美和犹太人对他的诅咒都归咎于他的希腊化政策。这种解释合情合理,与我们从古代文献中获得的印象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拉丁文化在公元2世纪处于衰落状态,塔西佗和尤维纳尔(Juvenal)是最后两位用拉丁文写作的大作家。与此同时,希腊文化却呈现蓬勃复兴之势。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始终对自己悠久璀璨的古典文化念兹在兹,视希腊本土在文化上独立并高于罗马。[5] 哈德良之热爱希腊文化,既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又为其推波助澜。他最早将希腊本土的希腊人劝说进罗马元老院,且直到他统治时期才有希腊人管理说拉丁语的西部行省(第305页)。哈德良显然是诚心诚意地将希腊人纳入统治阶级。可以不怎么夸张地说,他为希腊文化的繁荣所奠定的基础,最终导致罗马帝国蜕变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人后来骄傲地自称为“罗马人”(Rhomaioi)而非“希腊人”(Hellenes),恐怕不能说与哈德良的遗产毫无瓜葛。 不过,如果把哈德良的个性和癖好一律归咎于希腊文化影响,似乎有点求之过深。哈德良成年后蓄着精心修饰的胡子。伯利认为他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下巴没有刮干净的罗马要人,这表明他受到希腊文化、特别是爱比克泰德学说的熏染(第61、81页)。其实,虽然大多数早期罗马皇帝的肖像显示了光滑的下巴,但尼禄和图密善就留下了蓄胡的肖像。弗拉维王朝钱币上的王子也常常有胡子。另外,不应忘记,那些白色的古代大理石像原本是着色的,即使它们画有胡子,如今亦已铅华褪尽。 从古代起,哈德良的名字就与安提诺乌斯(Antinous)这个名字如影随形。后者是今日土耳其境内的一位乡村少年,他可能从123年起伴随哈德良左右,直到七年后在尼罗河溺水身亡。伯利主张,哈德良与这位娈童的关系,是年长的“爱者”(erastes)与年少的“被爱者”(eromenos)之间的希腊式爱情。考虑到哈德良对希腊文化的偏爱和安提诺乌斯本人是希腊人,这似乎言之成理。但应该看到,这种行为在罗马社会中司空见惯。许多罗马男子,不分贵贱,是当下术语所谓的双性恋,只要在性行为中担当主动角色,他们就不会质疑自己的男性气概。如果说这些人统统受了希腊文化影响,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真正让古代作家诧异的,不是这种关系本身,而是哈德良对安提诺乌斯之死的反应。他非但不顾及自己的身份而“哭得像女人”,还把诸多荣誉立即加给身份低微的安提诺乌斯。埃及流传一种古老的风俗:凡是溺亡于尼罗河中的人,都会如奥西里斯(Osiris)神一般复活,由此获得神性。哈德良先是鼓励埃及百姓将安提诺乌斯尊崇为奥西里斯的化身[6];几天后,又在他溺水附近建造了“安提诺乌斯市”(Antinoopolis),正是在这座希腊城市里发展出对安提诺乌斯的膜拜,安提诺乌斯开始被混同于希腊的酒神、林神、狩猎神等。这一膜拜传播极快,帝国东部说希腊语的许多城市甚至发行了有他肖像的钱币,而他的雕像和神祠遍布罗马帝国全境。存世的安提诺乌斯大理石像多达约100座,数量仅次于奥古斯都和哈德良本人的,已构成古典古代不可磨灭的遗产。这种膜拜能够迅速流行,当然与帝国各地城市想要借机向哈德良示以政治忠诚有关。然而,它是怎样流行起来的?这点以前并不清楚,但考古学家最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发掘已显示,希腊上流社会、尤其是最早一批进入罗马元老院的希腊元老,看来是这一膜拜的主要推手。[7] 尤可注意的是,安提诺乌斯膜拜并没有随哈德良的去世而告终,因此,尽管这种膜拜起初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但后来却得到不少说希腊语民众真心诚意的拥护。2到5世纪的基督教教父们曾对安提诺乌斯厉声讨伐,自然是把他当成了耶稣基督的竞争对手。无论如何,通过膜拜安提诺乌斯,希腊民众既强化了自己的希腊认同,又表达了对罗马的效忠,而这即使放在今天看,仍然匪夷所思。 除了安提诺乌斯,伯利还对哈德良周围其他人的生平交游详加考证。换言之,作者采用了“族谱学”(prosopography)的方法。这并不让人意外,伯利是罗纳德·赛姆的亲炙弟子,而赛姆是举世公认的用族谱学研究罗马史的集大成者。使用这种方法显然怀有一种信念:只有把皇帝本人放到他所属的社会群体中去,才能充分理解他。伯利在搜集与哈德良往来之人的资料方面可谓竭泽而渔,其用力之深之勤从书后长达16页的人名索引中可见一斑。在此基础上,他通过揭示这些人的籍贯、通过稽考他们彼此之间由联姻和收养而形成的亲属关系,来判断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影响,从而令人信服地再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社会交往和生存氛围。然而,族谱学的方法也对读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果对罗马人的姓名、对帝制时期的职官及官员的晋升程序(cursus honorum)缺乏较细致深入的了解,书中众多人名会使人生发汗漫无归之感。此外,这一方法虽然在研究人数较少的精英集团或信息较少的社会时能取得良好效果,但它往往忽略对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的探讨。而这在哈德良统治期间恰恰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罗马公民权在哈德良时期得以进一步普及,他发明了一种“大拉丁权”(Latium maius),一旦拥有它,城市市议会的所有成员(decuriones)都享有罗马公民权;而在以往拥有“拉丁权”(ius Latii)的城市中,只有卸任的城市行政长官才能得到罗马公民权。公民权的普及意味着公民权的贬值。为了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哈德良在司法领域内把帝国居民分为“上等人”(honestiores)和“下等人”(humiliores),此举最终取代了公民与非公民之分。[8] 哈德良在法律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举措,是统一了大法官(praetor)的告示,这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市民法。但这些重要内容在本书中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伯利要么完全忽略了它们,要么出于显然是研究方法的考虑而将之一笔带过。[9] 哈德良的性格在古人眼中是个谜。他平素好开玩笑,但并不招人喜欢。虽然坚持人有上下等之分,他却以亲民著称。他常常去公共浴室洗澡,有一次看到一个认识的老兵把前胸后背贴在墙上来回搓,一问才知此人退伍后生活拮据,身边没有奴隶服侍,哈德良遂把几名奴隶和养奴隶的钱一并赐给他;后来澡堂里好些老者当着他的面以身搓墙,他命人将他们带出澡堂,让他们互相搓到趴下。有的玩笑听得人笑不出来。他布下众多眼线监视朋友的私生活。有位妻子写信给丈夫,抱怨他成天流连澡堂,乐不思归。此人请求告退之际,哈德良提醒他别流连澡堂,他回答“我老婆肯定没把她写给我的东西也写给你!”哈德良是全才,诗歌、哲学、音乐、绘画、算术、占星、兵器、战略、账务样样精通。争强好胜难免流于刻薄。诗人弗劳茹斯(Florus)给他写过一首短诗,拿他的热衷旅行开玩笑: 我不要当皇帝,不要 ego nolo Caesar esse 漫步在不列颠人当中、 ambulare per Britannos —— <此行已佚> —— 忍受西徐亚人的霜冻。 Scythicas pati pruinas. 哈德良写诗回敬: 我不要当弗劳茹斯,不要 ego nolo Florus esse 漫步在小酒馆、 ambulare per tabernas 忍受圆鼓鼓的蚊蚋。 culices pati rotundas. “弗劳茹斯”希腊文谐音“φλα?ρο?”的意思是“琐碎的、庸俗的、无价值的”。《奥古斯都史》的作者认为,哈德良“集严峻与和蔼、尊贵与诙谐、冲动与迟缓、吝啬与慷慨、欺瞒与直率、残酷与仁慈于一身,并总是在一切事务上善变。”一言以蔽之,他的性格也是“躁动不安”的。这实在值得庆幸,我们从中知道这位皇帝既非正面英雄亦非反面恶棍,他不是某种刻板典型的化身,而是活生生的人,敏感、复杂得就像现代小说中的人物。 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哈德良作为皇帝的所作所为,阅读它仿佛步入一座哈德良的博物馆,伯利领着我们在每件展品前驻足讲解,但行至出口处,回望那些洁白、冰冷、闪着幽光的大理石像,遥想那缕跃动、飘荡的纤纤亡魂,我们不禁要问,刚才是否触摸到哈德良引起现代人共鸣的心灵深处?恐怕没有。哈德良传能否写出来的疑问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这里不得不提一本性质特别的书——法兰西学院三百年来首位女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尤瑟纳尔上世纪20年代沿地中海广泛游历,其间读到福楼拜一段话,说哈德良生活在一个罗马众神已无人信奉而基督教又尚未确立的时代,她大受触动之余,蓦然发现写哈德良就是自己的宿命。经过漫长酝酿和反复试写,她找到了切入口,决定为哈德良那部被历史黑洞吞噬的自传招魂。1951年,这本以第一人称写就的杰作终于问世。此书虽为小说家言,但向来为不少职业历史学家推崇,权威的《牛津古典辞书》第二版(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1970)“哈德良”条目下所附参考书目中就列有此作。[10] 尤瑟纳尔的书代表了一颗敏感的现代心灵尝试感知一颗古代心灵的最高结晶;而伯利是书资料齐备、考证精细,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哈德良生平的标准记录,为研究者所必读。
(Anthony R. Birley, Hadrian: The Restless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平装本;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陈筱卿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宋立宏,南京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犹太教、犹太史、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和历史,已出版译著、论著多部。
[1] Fergus Millar, “Review of F. Grosso’s La lotta politica al tempo di Commodo,”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6 (1966), p. 244. [2] 19世纪末在埃及Fayum地区发现了一份纸草残卷,上面几行希腊文被当作哈德良失传的自传,现藏芝加哥大学哈斯克尔东方研究所。此信表明哈德良自传写于他临终前不久,而且是写给其继位者安东尼·庇护的。可读内容的译文如下:“皇帝凯撒·哈德良·奥古斯都向他最令人敬重的安东尼问好。首先,我想让你知道,我正从生命中解脱出来,既不为时过早,也并非不合情理、令人遗憾、突如其来或官能受损,即使我看起来似乎——这我察觉到了——已伤及你,而你坐在我床边,不停安慰我,鼓励我挺住。因此,我感到我必须把下面这些写给你,以宙斯的名义,我不是要巧妙地画些庸俗的画、文过饰非,而是要直白、精确地陈述事实本身(……) 我的生父四十岁病死时是没有官职的公民,因此我已比他多活了二十年,并已快和我母亲的年龄一样大了……。” 参见Jan Bollansée, “P. Fay. 19, Hadrian’s Memoirs, and Imperial Epistolary Autobiography,” Ancient Society 25 (1994), pp. 279-281. [3] 汉语世界的译介,参看邢义田:《罗马帝国的“居延”与“敦煌”——英国雯都兰达出土的驻军木牍文书》,载氏著:《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2011年,第258-284页;宋立宏:《犹太集体记忆视域下的巴尔·科赫巴书信》,《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0-124页。 [4] 参看Mary T. Boatwright, Hadrian and the Cities of the Rom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 [5] 参看E. L. Bowie, “Greeks and Their Past in the Second Sophistic,” Past and Present 46 (1970), pp. 3-41. [6] 梵蒂冈博物馆现藏一座高241厘米的奥西里斯扮相的安提诺乌斯大理石像,图版参见Thorsten Opper, Hadrian: Empire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75-176. 三岛由纪夫对安提诺乌斯雕像的奇思妙想,参见三岛由纪夫:《安提诺乌斯》,载氏著:《残酷之美》(唐月梅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17-128页。 [7] Thorsten Opper, Hadrian: Empire and Conflict, pp. 168-193. [8] 参看Peter Garnsey, Social Status and Legal Privilege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9] 值得指出的是,在罗马史的特定语境中,学者们通常以宗族(gens)为单位,把属于同一个(或几个)宗族之人的生平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以揭示他们共同的背景特征,所以这里将“prosopography”译为“族谱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19、20世纪之交罗马史研究的主导范式由蒙森(Theodor Mommsen)奠定,蒙森系律师出身,特别善于发现法律制度对罗马史的影响。而以赛姆等人为代表的族谱学学派有刻意贬低制度因素的倾向,这其实是对蒙森所代表的那种范式的反动。学界近期对族谱学方法的反思,参看Averil Cameron, ed., Fifty Years of Prosop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 1984年,即《哈德良回忆录》英译本问世30年后,赛姆有感于它在职业历史学家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一一列举书中与史实出入之处,认为此书不是“历史小说”(historical fiction),而是“虚构的历史”(fictional history),与《奥古斯都史》类似。此演讲可视为史学界对此书的盖棺定论,参看Ronald Syme, “Fictional History Old and New: Hadrian,” in idem, Roman Papers V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 157-181. 该文发表于《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