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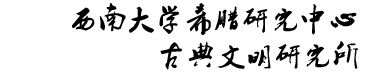
| 贾文言 王坤霞译:罗马帝国时期图像中的战争、奴隶制和帝国 |
| (发布日期: 2017-07-08 16:39:28 阅读:次) |
《古典学评论》第3辑 罗马帝国时期图像中的战争、奴隶制和帝国
菲利普·德·苏萨著 贾文言 王坤霞译
【编者按】菲利普·德·苏萨(Philip De Souza, 1964-),威尔士人,哲学博士,现为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古典学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时期的战争、海上航行和社会。已出版的专著有《希腊-罗马世界的海盗》(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la guerra del peloponneso)、《雅典与斯巴达:伯罗奔尼撒战争》(Atenas contra Esparta: la guerra del peloponneso)、《希腊人和波斯战争,公元前499-前386年》(The Greek and Persian Wars 499-386 BC.)等。曾主编《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和《战时古代世界:一部全球史》(The Ancient World at War: a global history)等。2000年,入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罗马帝国时期图像中的战争、奴隶制和帝国》一文原发表于《古典研究所通讯》(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2011年第1期,即该杂志的总第54期。在研究奴隶制、战俘等问题时,学者大多注重挖掘和利用分散于古代文学作品以及铭文纸草等所蕴含的史料。在该篇文章中,菲利普·德·苏萨并没有遵从大多数学者所依赖的史料来源,而是从纪念碑、纪功柱、壁画、工艺品等艺术品图像的角度,对帝国时期战败敌军作为俘虏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考察。在观点上,他指出罗马军事艺术中战败敌军作为俘虏的表现形式是突出而鲜明的主题,并且这是对罗马人将获取战俘是为了奴役他们这一战争的法定目的进行特别强调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虽然罗马帝国时期文化的很多艺术主题以及形式,都来源于或者深刻地受到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希腊艺术的影响,但是武士形象和战争场景在古风、古典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希腊艺术作品中是极为常见的,其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从希腊世界盛行的含混态度中得到解释。但是在元首制及其以后时期纪念性艺术的委托者在庆祝战争的获取性方面,尤其是在获取人力资源的艺术主题上,有强烈的偏好。作者从罗马人对战争、帝国主义以及奴役的态度和古代帝国文化中纪念性艺术的一般性特点两个角度,对罗马纪念性艺术的这种特征进行了阐述。接下来,请看作者是如何提出其论点并怎样进行阐述的。
本论文考察帝国时期罗马军事艺术中战败敌军作为俘虏的表现形式。文中将表明,其一,它们是突出而鲜明的主题,并且这是对罗马人将获取战俘是为了奴役他们这一战争的法定目的进行特别强调的结果;其二,尽管罗马艺术从希腊人那里获得大量的形象描述方式,但是在希腊艺术中俘虏和奴役的类似形象相对少见,因为希腊艺术并不怎么强调奴役战俘是战争的目的之一。与之相反,本文所涉及的元首制及其以后时期纪念性艺术的委托者在庆祝战争的获取性方面,尤其是在获取人力资源的艺术主题上,有强烈的偏好。从罗马人对战争、帝国主义以及奴役的态度和古代帝国文化中纪念性艺术的一般性特点两个角度,罗马纪念性艺术的这种特征将得到阐述。[[1]] 人们普遍认为,罗马帝国时期文化的很多艺术主题以及形式,都来源于或者深刻地受到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希腊艺术的影响。因此,赫尔舍(H?l scher)认为罗马人采纳了希腊化时代有关复杂战争场景的希腊传统,以庞贝城(Pompeii)著名的亚历山大马赛克和西顿(Sidon)的亚历山大石棺为代表,但基于他们自身展现胜者和征服的方式进行了改变,尤其体现在皇帝与战败的敌军的区分上。[[2]]他以重新用于君士坦丁凯旋门(the arch of Constantine)的图拉真带状雕刻带为例。带有皇帝的中部图景直接受到亚历山大时期绘画作品的影响。在这里,罗马人的描述再次突出了胜利者的优势地位:图拉真(Trajan)扫视了他面前的全体敌军,在他的对面没有与之对抗的指挥官出现。然而,最富感伤力的主题再次被插入:被割下的达契亚人(Dacian)的头颅由皇帝的士兵肆意地挥舞着,与四处逃窜的敌军难以区分;或者是一个死者倒卧在不断向前延伸的马道上。[[3]] 武士形象和战争场景在古风、古典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希腊艺术作品中是极为常见的。尽管现存的古风时期的公共或纪念性艺术品样例不多,但不管怎样,俘虏或战俘并不是常见主题。私人艺术的主要类型,诸如带有绘画的陶器和墓室壁画,经常出现被征服的敌军,但是他们被刻画为勇士,而不是战俘。对于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我们有更多的公私艺术品的样本,但同样的一般性结论仍是适用的。在那些时期遗存下来的数以千计的作战景象中,战争场景是普遍的,但随之而来的捕获和奴役战俘并不是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希腊战争图像中的常见主题。当然,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有发现,如桑索斯(Xanthos)涅瑞伊得纪念碑(the Nereid monuments)上的浮雕雕刻带,即插图2,或者是在少量的陶器绘画上也有发现,但这些题材似乎都局限于捕获成年男子,他们曾经是士兵或政治领袖。[[4]]没有涉及到妇女、孩童或其他明显的非战斗人员。 希腊艺术中捕获和奴役景象少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从希腊世界盛行的含混态度中得到解释。我们知道,早期的希腊人通常奴役战争中的俘虏,有时将整个城邦或甚至是整个地区的人口作为战利品,例如斯巴达人在公元前八世纪晚期的某些时候把美塞尼亚人(Messsnians)都降至奴役的地位。在最早的希腊叙述性文献《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由战争和抢劫而获得的俘虏明显地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实际上,获取奴隶是这些好战的巴塞琉斯(basilees),如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基琉斯(Achilles)以及奥德修斯(Odysseus)等参战的首要原因之一。虽然如此,在古风时代的晚些时候,由希腊人的邻人奴役希腊人的情况已经逐渐减少。在希腊城邦,以及在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王国内部,奴役希腊人通常得不到宽恕。古典时代雅典的文献所给出的印象是,绝大多数的奴隶都来自于蛮族之地,如斯基泰(Scythia)、色雷斯(Thrace)以及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虽然如此,但历史著述的记载表明,希腊世界内部战争的胜利者通常决定战败者的命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一命运包括强制奴役作战者以及非战斗人员。[[5]]尽管如此,希腊人似乎支持一种鼓励其他对待战俘方式的道德和政治观念,这些方式包括:解除武装和释放,赎回或者重新安置,并且阻止其他极端行为。[[6]]在色诺芬的记述中,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Agesilaos)曾言“迫使希腊的城邦警醒即可,而不是使其成为奴隶。”[[7]]但是,他对于奴役蛮族人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可从公元前396-395年他征讨波斯时脱光战俘的衣物并将战俘出售可见一斑。[[8]] 也许可以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希腊艺术比古典时代的希腊艺术,在对待他们失败后的被征服者问题上展现出更高程度的兴趣。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可以援引著名的用于纪念加拉提亚人(the Galatians)失败的群雕。加拉提亚人是塞琉古王朝(the Seleucids)的盟友,这一群雕是以帕加马王国(Pergamon)的国王阿塔路斯一世(King Attalos Ⅰ, 241-197BC)的名义而建。有几座高卢群雕像(Gallic’ statue groups)曾树立在雅典(Athens)、提洛(Delos)、德尔菲(Delphi)以及帕加马(Pergamon)。[[9]]与此同时,事实是这些给人印象深刻的雕塑作品的原件并没有留存下来,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后来的复制品,它们聚焦于被打败的蛮族人而不是他们的希腊获胜者。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去颂扬战胜者,而是通过让参观者看到被打败者是英勇的蛮族人,从而使参观者把自己想象成获胜的阿塔路斯以及他的兵士。费里斯(Ferris)谈及最为有名的一件雕像,有人称其为“垂死的高卢人”(the Dying Gaul),或谓“小号吹奏者”(the Trumpeter),由现藏于罗马卡皮托里尼博物馆的一件复制品完美地得到展现:“看到这一雕像时,只看到他孤立地被留在战场上如其他人一样死去,却没有看到失败时的尊严是几乎不可能的。” [[10]]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群雕中所展现的形象并没有被特定地刻画为俘虏,或者是未来的奴隶。而是把他们刻画为即将赴死的勇士,他们选择有尊严的死去,而不是被奴役。在路德维希群雕(Ludovisi group)中一名首领即是如此,同样的选择很明显地也赋予一名非战斗人员的妻子。这些希腊化时代的雕像会唤醒参观者的崇拜,甚至可能是参观者的恐惧,但无助于引发怜悯,更与鄙夷无关。我们需牢记它们在罗马帝国时期被大量的复制以及传送的事实,尤其是考虑到罗马人在那些地区减少了对战败者形象的颂扬。[[11]] 在与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作战时,罗马人展现了对于战俘的看法,它们形成于征服意大利时期,明显的不同于与他们的希腊人盟友及其反对者所拥有的共同观念。[[12]]罗马人对待那些俘获者或者已经投降于他们的人的方式,以坚持投降行为(deditio)意味着无条件接受罗马人有权任意处置其命运(deditio in fidem populi Romani)的原则为特征。因此,所有的俘虏都完全处于无权地位,除非罗马人民,或者在更多情况下是罗马人民的代表,也即获胜的罗马指挥官,同意稍微地改善其地位。[[13]]笼统地说,这一观念与希腊人所认为的俘虏的命运归于捕获者的看法是相类似的,但在实践过程中,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倾向于残酷地对待战俘。这一文化背景冲突的文字证据,来自于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对公元前220-公元前167年之间的历史进行叙述时,他通常会对战争中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道德观念进行比较。 [[14]]公元前210年,罗马人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Philip Ⅴ of Macedon)处于战争之中,当时的一名罗马代执政官(proconsul)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攻取了埃吉那(Aigina)。让埃吉那人以及其他很多希腊目击者惊诧的是,加尔巴起初拒绝了任何战俘去筹集赎金。正如下面这则取自波利比乌斯记述的节录所表明的,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所期望发生的和希腊人所期望的有着较大的差别。[[15]]波利比乌斯暗指罗马人在遵循他们的惯例,但是这与希腊人的通行规范是相违背的:
“罗马人占领了埃吉那,那些没有逃脱的埃吉那人集聚在船上,并请求代执政官允许他们派出使者到同种族的城市筹集赎金。普布利乌斯起初断然拒绝,并声称他们应该派遣使者去处境更好的城邦那里,请求前来并拯救他们,与此同时,他们现在依然是自由的而不是奴隶。不久之前,他们甚至不会屈尊去答复他的使者,而现在他们既然已经落入他的手中,此时却要求准予派遣使者去同种族的城市那里这是最为愚蠢的。所以,此时他驳回了那些带着这种言辞前来与他接洽的人,但是在第二日召集所有的战俘(aichmalotai)后,他说他没有义务宽恕埃吉那人,但为了剩余的希腊人他将准许埃吉那人派出使者去筹集赎金,正如这是他们的风俗(ethos)。” [[16]]
而随后所提及的埃吉那人都降为奴隶(pantas exendrapodisato)则表明加尔巴表面的让步只是一种象征性姿态,很可能是为了抚慰他的希腊盟友。 [[17]] 这一问题的意义由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的行动而得以彰显。他极为重视代玛人(the Dymaean)的赎回问题,他们的城市曾在公元前208年被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所攻取,然后将故土归还给他们(李维,32.22.10)。通过这样做,菲利普向其他的希腊人表明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他尊重他们的风俗和价值观,而在某种程度上罗马人并不遵从。当波利比乌斯将如下几点插入到公元前207年一个不知名的使者在希腊集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时,他强化了希腊人共有的观念与蛮族罗马人的看法之间的差别。这一演说的一个关键主题是批评埃托利亚人(Aitolians)与罗马人结盟反对菲利普五世以及他的希腊盟友:
然后,菲利普是战争的名义托词;他并不是危险(对于埃托利亚人而言);而是因为他是伯罗奔尼撒的绝大多数城邦、彼奥提亚人(the Boeotians)、优波亚人(the Euboeans)、佛基斯人(the Phokians)、罗克里斯人(the Lokrians)、色萨利人(the Thessalians)以及伊庇罗得人(the Epirots)的盟友,你们结盟(与罗马)反对他们所有人,结盟的条款规定他们的人力以及私人财产应属于罗马人,而他们的城市以及土地则归埃托利亚人。过去,你独立攻掠了一个城市,你将不会准许你们去激怒自由人或者去烧毁他们的城池,因为你认为这是残暴的过程并且是不合乎文明的。但是,你已经通过结盟将剩余的希腊世界都让与了蛮族人,把他们推向残忍的愤怒和暴行。此前,人们没有领悟到这个问题,但现在俄雷昂人(Oreion)以及不幸的埃吉那人的例子已经将所有的问题向你暴露出来,正如财富自有其目的,但却引发了你的迷恋。 [[18]]
演讲者可能是罗德斯人色拉西特拉特斯(Thrasykrates),是波利比乌斯表达其道德和政治观点的代言人,他明确了希腊共同价值观的至高无上性,据此埃托利亚人理应与其同胞希腊人共命运,也即应该与罗马人断绝关系。[[19]]波利比乌斯无疑使读者意识到希腊人要比蛮族的罗马人更文明,尽管他们的自身行为在之前的战争中经常达不到这一文明标准。 在现代学者看来,罗马人具有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具侵略性和好战的共同体之一的名号。这一名号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战争和征服中获得的成就——他们被认为是古代最为成功的帝国缔造者——新近的历史学者已经通过分析他们的军事和帝国主义文化来解释其成功的原因对此予以了强调。[[20]]大规模的奴役是罗马人在西班牙、北非以及希腊化时期东方战争的特征。[[21]]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公元前167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lus)洗劫了伊庇鲁斯(Epeiros)的城市和集镇,据说结果是15万人被奴役。[[22]]在公元前146年,罗马的军队劫掠并破坏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两个最大的城市,即科林斯和迦太基,将男性居民残杀殆尽,而妇女和儿童则被卖为奴隶。[[23]]这些征服和奴役的战争为随后几个世纪罗马的帝国扩张提供了范例。[[24]]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没有奴役战败者,在很多场合下这些战败者还包括来自其他城邦的希腊人,而是存在强烈的不将此作为战争公开目的的文化压力。从古典时代早期希腊文献和哲学讨论就强调异族人,或蛮族人内在的奴性,他们由国王统治,区别于自由的希腊人,他们的政治架构甚至是为了最佳效果而依赖奴隶。[[25]]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通常被唤作是战争的目的,犹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但社会自由并不如此。[[26]]这些优先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艺术并不强调对敌军的捕获和奴役。在罗马艺术中,特别是在公共和纪念性艺术中,通常为罗马民众展现帝国时期征服中受害者的形象。为了理解它们处于显要位置的原因,我们可以转向考察罗马军事制度最为著名的一个方面——凯旋式。 罗马的凯旋游行由宗教仪式演化而来,在这一仪式中获胜归来的将军前往国会大夏的朱庇特神庙(the temple of Jupiter),以便奉献用以致谢的牺牲。这一仪式似乎是源于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的先人,但是无法肯定地断定它怎样起源以及最早发生在哪里。明确的是,在成为罗马领导人主要庆祝其军事成就的方式之前,这些面向将军及其军队的归国行进游行已经缓慢演进了几个世纪。[[27]]在共和国的中期和晚期,凯旋式会持续几日,因为元老贵族的主要成员要向民众展现他们的个人荣耀。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在位)将全面的凯旋式只限于皇室家族,部分原因是由凯旋式所积聚的颂扬和声望会提升政治影响,而这可能打破元首制时期内在的权力平衡。 对于罗马民众而言,凯旋式是他们观望领导者运用归于其支配的军事力量所取得成果的绝佳机会。尤其是民众特别期望看到都是取得了什么战利品。这典型地包括俘虏的代表群体,如成年男子、妇女、甚至是由罗马人捕获并带回意大利的儿童。在凯旋式中展现的最为重要的俘虏无疑是敌方的领导者——国王、王后、将军以及首领,他们的军队已经被获胜的受到凯旋仪式欢迎的人所征服。次要的政治领导者和家庭成员的近亲也囊括其内。如公元前167年,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展现了保持沉默的马其顿国王柏尔修斯(Perseus),与他一起的还有他年幼的儿子和女儿。[[28]]多次出现的战败者领导人,如米特里达梯六世(Mithridates Ⅵ)和克莱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Ⅶ),选择了死去而不是接受俘虏游行中众目睽睽下的羞辱。在某些时候,死亡是敌军将领的归宿,正如高卢的领导者维尔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所证实的,他在公元前46年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凯旋式中被杀死,[[29]]或者是西蒙·巴尔·吉拉斯(Simon Bar Gioras)被带走并被施以绞刑,以此作为公元71年维斯帕芗(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结束祭献仪式的前奏。[[30]]一名自重且保持尊严的战败者将领,如条顿人(the Teutones)的国王条顿波都斯(Teutobodus),他在公元前101年马略(Marius)的凯旋式中以这种形象出现,有可能赢得罗马民众(不情愿的)尊重,[[31]]但游行中可能还有几百名地位较低的俘虏。[[32]]他们在言语上和身体上受到看管者或者也可能是旁观者的伤害。他们带着镣铐犹如奴隶,他们或被处死、或对于大多数而言可能是终生受奴役。我们可以认为除了展示战败者的全体人员,这些战俘也给予了罗马旁观者将他们一睹所有人力战利品样本的机会——大量的战俘将充斥意大利的奴隶市场。[[33]] 随着罗马财富和权势的增长,罗马的将军通过资助建立纪念其功绩的纪念碑、神庙以及其他纪念物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胜利战争,它们中的很多都饰有绘画和浮雕雕刻。霍利迪(Holliday)认为永久纪念物上对战争以及胜利场景的描述将有助于使罗马参观者认为持续的战争努力是正当的,以及通过他们所能看到的,而不是仅仅听到或者读到的罗马疆土,来给予他们满足感。[[34]]不是所有的战俘展示都能被认为是意味着对罗马敌人的奴役,但是至少一些凯旋纪念物上的俘虏形象必定是大量奴隶的象征,他们是罗马帝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俘获敌人的主题,通常是北方或者东方的蛮族人,是奥古斯都时代以来罗马纪念艺术的突出特征。与此同时,可能类似的形象在共和国时期的纪念艺术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突出主题。与之相反,现存的样本清楚地表明,早期元首制时期在纪念罗马帝国战争的艺术形象表达方式上,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主题出现,即在与庆祝军事胜利相联系的背景中展现了战俘。被缚的俘虏在罗马纪念碑下方是奥古斯都时代战争艺术中不断出现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早期样本存在于凯旋门饰带的遗存残片中,这一饰带曾一度装饰在罗马城古剧院旁的阿波罗神庙(the temple of Apollo Sosianus)里,可追溯至公元前25年,参见插图3。这个残片上有一对被缚的蛮族奴隶,一男一女,坐在胜利纪念碑的下方。他们被放在一个抬东西的框架之上,即将被游行中的六个侍从抬起和抬走。可能这是公元前29年屋大维凯旋式中的一个场景。神庙的建造者是盖尤斯·索西乌斯(Gaius Sosius),他曾经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加入到安东尼(Antony)的阵营并在亚克兴海战中为其效力,所以他通过为在伊里利亚(Illyria)庆祝屋大维击败“蛮族”敌军的胜利提供饰带装饰来表明他对于新政府的忠心。[[35]]类似的出现在罗马纪念碑下部的成群被缚或捆绑奴隶的雕刻,也装饰着位于拉·图尔比(La Turbie)和圣·贝特朗(San Betrand)的奥古斯都纪念碑。 [[36]] 捕获或者处理奴隶的场景不仅在纪念性的、公共的艺术上可以找到,而且也明显表现在私人委托制作的物品上,是为了那些不太显要的陈列,例如装饰性的浮雕珠宝装饰物和私人居所墙壁上的湿壁画,但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公共展示和私人展示之间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罗马最重要元老和罗马皇室家族成员的家是公共空间,在那里,宾客和友人得到款待,并且主人所珍视的艺术品都是面向挑选后、政治上非常重要的观众。在私人艺术中,奴役敌军主题的采用可由公元10年著名的奥古斯都宝石(Gemma Augustes)下方图案的类似形象得到证实。在罗马,这可能是为奥古斯都家族的成员和他们在元老贵族中的密友,所制作的众多精致艺术品中的一件。这一装饰物的上端,是奥古斯都以朱庇特形象出现的场景,他坐在罗马女神(the goddess Roma)的旁边并欢迎两位获胜的将军,一位可能是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而另一位是提比略(Tiberius),他们正跳下战车(biga)。在独立的、下方图案中,装饰物描绘的是,士兵在一群坐在地上、被缚的男女蛮族人中间树立起纪念碑,这极易使人想起罗马古剧院旁阿波罗神庙的浮雕,与此同时,第二批俘虏也被拖拉到他们这边。[[37]]值得注意的是,在奥古斯都宝石中,奥古斯都、提比略以及日耳曼尼库斯都被置于上部,并完全与战败的蛮族奴隶和士兵区分开来,强调了罗马军事艺术中等级制的一面和罗马精英人物的优越地位,他们被与奥古斯都和平(Pax Augusta)的安全与富足相联系的形象所包围。这些形象包括海神(Oceanus),与象征富裕的康纳科佩及孩子在一起的特鲁斯(Tellus with Cornucopia and childen),罗马女神以及胜利女神(Victoria)。 [[38]]这两个图案结合起来看,就是在下方图案中俘虏的征服和悲痛以及众神的佑护,支撑着上方图案中皇帝、他的家族以及罗马人民的权势、繁荣以及幸福。[[39]] 一个不太公开的战败敌军屈从于胜利指挥官的私人形象,可以在罗马台伯河岸边的法尔奈希纳别墅(Villa Farnesina)中装饰走廊的精致且给人印象深刻湿壁画的众多场景中可见一斑,可参阅插图4。法尔奈希纳别墅很可能属于奥古斯都右侧的人,即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如果不是为阿格里帕实际建造的,那可能也是为其而装饰的,因为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亚(Julia)在公元前19年嫁给了他。 [[40]]这一场景的主题是一场至少涉及6艘战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海战。它发生在一个岬角的外海,在这一岬角之上是坚固的防御工事,也可能是带有城墙的城市,正处于被围攻之中。除这一工事外,在这一场景左下角的底部,有一名或两名被绑缚的战俘正被带到一名穿礼炮的人面前,他手持标枪或者棍棒或权杖之类的东西。在罗马世界,标枪(hasta)能被用来看作是合法拥有的象征,同理,当奴隶被解放时他们将触摸棍棒(festuca)。起初,标枪只是表明物品是战争战利品的事实,或者是通过权威性权力的行使来获得。因此,不管这一人物是持有标枪、还是棍棒、抑或权杖,都可能是对俘虏正式所有权的象征。[[41]]对这一带到获胜指挥官面前的失败敌军的大体勾勒,看起来几乎是作品的事后之笔,尽管如此,这似乎意味着对于罗马资助者而言,投降和屈服已经成为战争图像的典型内容。对被征服战俘的展现服从于塑造完全胜利的形象。 这一不断出现的主题展现给罗马观看者的是,通过帝国的征服获取奴隶是所能触摸得到的战争目的。通过战争获得奴隶因此紧密地等同于皇室家族的权势和威望,他们迅速地成为罗马的流行图标。当然,奴役或屈服的形象,在奥古斯都纪念对于蛮族人胜利的纪念物品中,并非是唯一的发现。来自古剧院旁阿波罗神庙的一些浮雕残片,描述了一次战役中的高卢骑兵与罗马骑兵。现存于曼托瓦(Mantova)的一浮雕残片上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战争场景,很可能属于罗马奥古斯都神庙的门面,或许是广场中卡斯托尔(Castor)和伯里克斯(Pollux)的复原神庙。它对战斗中罗马骑兵战胜高卢武士的描述,是极不同于前述希腊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传统的。费里斯注意到它与阿塔里德雕塑(Attalid sculptures)在很多地方相似。它关注战争时刻,并且将罗马的高卢仇敌描述为强壮的、勇敢的以及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 [[42]]考虑到现存的奥古斯都时代物品的相对缺乏,除了那些强调失败和征服的物品外,可能存在更多、相似的描述。[[43]] 虽然如此,通过考察公元81年奉献的提图斯凯旋门(插图5),我们能够体会到奥古斯都以后罗马帝国时代艺术中对战败、奴役敌军展示的持续重要性。它是古代罗马最为知名的胜利纪念碑之一,提供了一个有关罗马战争图像的极好范例,因为它纪念了帝国的胜利和他们的战果。凯旋门内侧的两块高处的雕刻带展现了公元71年皇帝苇斯巴芗(Vespasian,公元69年至79年在位)以及他的儿子提图斯(公元79年至81年在位)在公元66年至73年犹太战争中他们获胜后的胜利景象。[[44]]一块雕刻带表现的是皇帝乘坐他的战车,前有执束棒的侍从,并有胜利女神相伴。对面的雕刻带突出了市区游行时在罗马民众面前展现的掠夺物以及战俘。[[45]]这些景象形象地表达了皇帝在战争和和平中的主导地位。作为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者和共和国(res publica)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他负责战利品的分配,尤其是敌军俘虏和被奴役的人。 正是在苇斯巴芗和提图斯统治时期,罗马获得了帝国权力基于战俘和奴隶最为著名的纪念物——弗拉维安竞技场(Flavian Amphitheatre),更多是以圆形剧场而知名。这一圆形剧场可被看作是皇帝在罗马帝国范围内对于每一个人权力的终极象征,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战争中被捕获的人而言更是如此。罗马大竞技场中展现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角斗士的格斗中或类似的斗争中,仪式性地处决被俘的敌军武士。对此,卡西乌斯·狄奥在公元80年圆形剧场落成典礼的叙述中有所描述:
在那里,有鹤之间以及四只大象之间的争斗;无论是野生的动物,还是驯养的动物,它们被杀死的数量达到9000;妇女(不是那些地位高的人)负责处理它们。对于男性而言,几个人参与一场搏斗,几组人在步兵和海战中斗争……这些场景在上演,并将持续100天;但是,提图斯也为民众提供了一些实用的东西。他会从高空抛向剧场各种小木球,上面刻有或食物,或衣物,或银质饰品或也可能是金质饰品,或马匹,役畜,牛或奴隶。那些抓取它们的人可以籍此到奖赏领取处,从那里他们可以领到所标明的物品。[[46]]
不是只有皇帝可以处置敌军俘虏。奥古斯都时代的叙事和文件来源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元老贵族在参与追求罗马的帝国主义政策方面存有持续的重要性。具有这种意愿和具备成为所谓“军事人员”(viri militares)能力的元老贵族赢得了属于他们自身的、有限的荣誉,前提是他们没有对皇帝的权威构成挑战。[[47]] 帝国时代公共纪念物上的图案,反映了罗马民众希望从他们的领导者那里得到什么,而那些领导者,尤其是皇帝,也知道什么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威望和权威。对于普通罗马士兵和公民怎样看待罗马的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人力战利品,我们拥有的直接证据较少,但是纪念战争的纪念物中征服和奴役形象的盛行意味着广泛共识是不能否认的。这一共识也体现在日常用品上的形象上,例如公元1世纪出土于塞浦路斯(Cyprus)的赤陶灯具,饰以一对蛮族俘虏夫妇在一罗马奖杯下面的画面,或者公元2世纪来自埃及的小雕像,绘有一名罗马士兵,可能是皇帝图拉真(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他抓住敌方武士的头发,并以剑相威胁(插图6-7)。[[48]]尽管一连串的此类素材远超本论文的有限篇幅,可以断言,这一现象正如布拉德利所论述的,具有广泛的地理性,他除了援引出土于中部希腊的卡瓦拉(Kavala)的青铜灯,还援引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提帕萨(Tipasa)的一幅马赛克,前者是以被缚的蛮族战俘的形式展现的,后者表现了一对俘虏夫妇及其孩子。[[49]] 如果我们考察图拉真纪功柱上饰带中对战俘的展现方式,这一纪功柱落成于公元113年(插图8-9),对刻画奴役战败敌军相对重要性的认识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在描述性饰带的几部分中,男子、女性以及孩童的抓获被描述为图拉真对达契亚人战争的一部分。不过于强调这一主题是重要的,虽然如此,也需承认这是此类战争的正常结果,但它不是它们唯一的突出特点。例如,图拉真纪功柱的最后一个场景表现了达契亚的老年男子、妇女以及孩子被强制地迁移,尽管位于记功柱顶部的这一部分饰带已经几乎完全被雨蚀风化。[[50]]因此,尽管承认这一场景是庆祝罗马人胜利的最终结果,但是它处于几乎看不到的位置,表明归之于这一外观的重要性也并不突出。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大纪念碑(the great Tropsion),或者是胜利纪念碑,它大约是公元109年为纪念达契亚战争而在阿达姆克利西(Adamklissi)树立的。在这里,以比图拉真纪功柱中优美雕刻饰带更为简略和直接的方式,把对达契亚人的征服和制服展现给那些直接经历过此事的人。[[51]] 罗马人对于征服被捕获、地位低下敌军武士和非战斗人员的庆祝形象,并非是同一的,不管怎样,而是在各个纪念物之间存在相当的差异。惠特克(Whittaker)已经就众多这类征服形象(男性压倒女性)中强烈的性别性质进行了评述,他强调马尔库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 公元161年至180年在位)皇帝纪功柱中俘获和毁灭的景象要远比图拉真纪功柱上的更为暴力和对毁灭的表现更为显明(插图10)。俘获敌军武士斩首行为和对妇女儿童的暴力抓取的逼真形象是其特征,尽管长期奴役的观念暗含在这一纪念物的一些场景之中,这一纪念物的年代可以确定为公元180年。 [[52]] 这些描述中残暴、具有破坏力的方面,使人想起历史学家塔西佗通过不列颠人的领袖卡尔加库斯(Calgacus)谴责罗马帝国主义的演说所引发的感伤。这一演说发表于他对公元83年格劳庇乌斯山战役(Mons Graupius)中尤里乌斯·阿古利可拉(Julius Agricola)胜利的记述之前:
“他们洗劫了世界,并且不久之后,当所有土地因为他们的劫掠而遗弃时,他们又开始在海上搜寻。假如敌人富有,他们的贪婪驱使着他们,或者假如他们贫穷,他们便会渴望荣誉。东方不能使他们满足,西方亦是如此。他们是仅有的在苛求财富和贫困方面都保有同等热情的人。以他们所谓的‘帝国’之名,他们劫掠,他们谋杀,他们奸淫。而在所到之处开了小差,他们便称之为‘和平’。”[[53]]
这篇演说和如此形象提醒我们:无论是罗马平民,还是元老精英,他们都充分地意识到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黑暗面。 在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公元193年至211年在位)凯旋门雕刻装饰中,我们能够看到捕获和奴役在罗马战争图像中的持续重要性。这一规模庞大的胜利凯旋门在公元203年树立在罗马广场(the Forum Romanum)的中心地带,是为了纪念皇帝的功绩,“因为他恢复了罗马国家,并通过他们在国内外展现出来的美德来拓展了罗马人的帝国。”[[54]]皇帝明显是将自己与内战后共和国最知名的恢复者——奥古斯都相比较。孔利(Cooley)的新近研究,强调了奥古斯都和塞维鲁在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他们尤其是在罗马城所选择的向罗马民众展现自己及其成就的方式上的相似性。她认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将自己与奥古斯都以及朱利亚-克劳狄王朝的功绩和声望相比是有意为之的。作为这一尝试的一部分,他选择将他的用于纪念远胜于奥古斯都的微小外交胜利的对帕提亚人胜利凯旋门,置于罗马广场中奥古斯都的凯旋门的对角线上,且这一凯旋门是一个三拱道的建筑。[[55]] 甚至可能是,塞维鲁凯旋门的图像中对被缚帕提亚人以及被毁城市的描述,不仅反映了有关和平的新观念(正如罗斯所强调的),而且可能是暗指他赢取了比奥古斯都更具决定性的胜利。相比之下,奥古斯都凯旋门中的帕提亚人还保有些许尊严,假如我们能够相信他凯旋门上的铸币图案,在那里他们都出现在奥古斯都所乘战车的两侧,正向他致敬。 [[56]] 凯旋门雕刻装饰的主题是这位皇帝的军事成就。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选择与他的获胜军队紧靠在一起,犹如图拉真在他的纪功柱中所做的,也犹如马尔库斯·奥里略在他的纪功柱以及凯旋门雕刻带中所体现的。[[57]]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凯旋门雕刻带的主要部分,以夸张、或者某种程度上有点凌乱的方式,展现了罗马军队在斗争中打击帕提亚人的场景。在这些场景的下方,较小的雕刻饰带描绘的是行进中的士兵正引导被俘获的帕提亚人向罗马女神走去。还有夺取战利品以及帕提亚自身战败人物的形象。它们明显地意指帝国胜利的组成部分,尽管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是否真正地在庆祝他对帕提亚人的胜利的出处尚不明确。虽然如此,在凯旋门底部的大型雕刻带上,将对敌人的征服和奴役作为罗马人胜利的结果,是有着清晰视觉表达的。 [[58]]在这里,身着披风和蓄有胡须的罗马士兵引导着被缚的帕提亚人,他们穿着裤子和戴着弗里吉亚帽子(Phrygian caps),这肯定是将之作为通过罗马广场的庆祝胜利的游行俘虏的永久代表。这些几乎与真人同大小的形象,是使那些到广场处理其事务的罗马公民认识到罗马征服代价与利益的最为生动的提醒。他们也可能将奴隶形象中固有的讽刺意味视为帝国权力象征的基础。 在这一时期,对征服蛮族人主题的偏好也见于阿根塔伊凯旋门(the Arch of the Argentarii),它于公元203年12月到公元204年12月之间的某个时间树立在屠牛广场(the Forum Boarium)的北部。它由贩卖牛的商人和放债人(argentarii)联合奉献,他们在这一商业区域从事活动。他们所选择的雕塑装饰展现了他们对新王朝的忠诚,并且提供了一个接受塞维鲁帝国形象的范例,而这一形象可从新近树立在罗马广场上的凯旋门上见到。对塞维鲁权力的军事强调由西侧台基上两名罗马士兵和两名蛮族捕获者来彰显,帕提亚人可根据他们的服饰来确定,而罗马士兵则可根据南面壁柱上饰有皇帝及其儿子们肖像的禁卫军旗帜来辨别。[[59]] 对罗马城外战俘的描述存有相当变化。在大莱普提斯-麦格纳(Leptis Magna),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出生地,也是通行拉丁语的城市,在那里树立的凯旋门所描述的内容包括很多男性和女性捕获者在纪念胜利的游行队伍中被牵引着,或者被放置在框架上抬着。这一形象与上述所谈及的来自罗马和西部行省的奥古斯都时期的实例是相似的。[[60]]对战败者更为尊严形象的持续吁请的典型范例,是罗马时期科林斯广场的“俘虏门面(Captives Facade)”。这一纪念物通向罗马的一方形建筑(Roman basilica),它建于公元160-170年,其特征是四位身着帕提亚服饰战俘的巨型雕像(插图12)。这里是希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离阿波罗神庙只有几码之隔,我们看到对罗马权力(并且是希腊的?)优越于蛮族人进行颂扬图像的偏好,即通过展现蛮族人作为征服实力的象征——这一形象更多地与前述希腊化的传统相一致。 尽管如此,甚至在科林斯也存在对帝国主义者控制局势类型进行艺术描述的自由空间,我们看到这在罗马城是极为普遍的。女像柱基座雕刻的浮雕,所描述的是男性俘虏和女性俘虏分居一个小型纪念碑的两侧。其中的一名女性俘虏用大腿托着小孩(插图13)。第二个柱基上的雕刻,所表现的是一名罗马将军,可能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正从胜利女神那里接过桂冠,与此同时,在他身旁则站着一名反绑着手的蛮族人。[[61]]这些景象的基本部分,与罗马古剧院旁阿波罗神庙浮雕中奥古斯都的形象、拉·图尔比和圣·贝特朗的纪念碑以及奥古斯都宝石,是极为相似的,但是它们的小尺寸和从属地位可能是对征服和奴役敌人主题的兴趣更为弱化的表现。我们不知道是谁决定了纪念门面的装饰方案,但是罗马和西部行省的同时代纪念物并没有此类遗存。然而,在对这两个图像主题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过度解读方面,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并设想那是考虑到了希腊的感受敏感性。位于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的塞巴斯泰昂(the Sebasteion)纪念浮雕有几处范例,其特征是朱莉亚-克劳迪王朝的皇帝英勇地征服甚至是杀死蛮族行省的人。[[62]]与之相似,在以弗所(Ephesos)的安东尼祭坛(Antone Altar)展现了战败帕提亚人的凯旋形象。与塞巴斯泰昂一样,这是宗教性的纪念物,它对皇帝们的权势和人身关注甚多,卢基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以及同僚安东尼(Antonine)即是如此。[[63]] 尽管在公元3世纪晚期和公元4世纪早期有众多政治、文化以及宗教变化,罗马战争图像中征服和奴役主题的延续还是非常明显的。称之为诺瓦斯凯旋门(Arcus Novus)的四帝共治早期纪念物的部件,所表现的是一名罗马士兵牵引着一名被缚的蛮族人,而另一名蛮族人则跪在带有胜利女神的纪念碑前。诺瓦斯凯旋门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对克劳迪雕刻部件明显的重复使用,这些部件可能来自于一个庆祝克劳迪在大不列颠胜利的纪念物。 [[64]]不断重复的形象可追溯至奥古斯都时代,并且公元1世纪的材料运用到公元3世纪晚期的纪念物上表明从元首制时期到帝国晚期罗马人在胜利、征服、制服以及奴役蛮族敌军方面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基本的连续性。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君士坦丁凯旋门更为生动地予以展示了,该凯旋门于公元312年在元老院的授命之下完成,邻近大斗兽场,主要是为了纪念君士坦丁新近从他的竞争者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那里解放城市。这一雄伟壮观的三拱道凯旋门饰有浮雕雕刻带、雕塑以及来自于原本是纪念马尔库斯·奥里略、哈德良和图拉真的纪念物上的圆形图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65]] 这一纪念物上的很多再次使用的图案特征或意指的是罗马传统蛮族敌人的失败和奴役,而不是君士坦丁(公元306年至公元337年在位)最近为了掌控罗马而打败的内部敌人。主拱内部的一个雕刻带展现的是君士坦丁(原初是图拉真)在士兵的护卫下踏着倒下蛮族的尸体冲入战斗,而一些士兵则手持被杀死敌军的首级。然而,在雕刻带的上部铭刻着“Liberatori Urbis”(致城市的解放者),明显的是指马克森提乌斯的战败。一块相似的雕刻带上,铭刻的是“Fundatori Quieties”(致和平的创建者)。[[66]] 其他的雕刻带表现的是皇帝(起初是马尔库斯·奥里略)坐在法官席上,与此同时一名蛮族将领和一个年轻人则祈求他的宽恕,或者是表现罗马士兵引导着被捕获的男性蛮族人,以及被缚的男性、女性以及孩童坐在胜利纪念碑之下。达契亚蛮族人的雕塑,可能是来自于图拉真广场,与科林斯的捕获者正面中的帕提亚战俘有几分相似,但是他们并不让人感到更值得怜悯,而是有着更为威严的外表,反映了他们在图拉真时代作为难以对付的对手的地位。可能他们出现在君士坦丁胜利纪念物上,以及其他被打败和祈求怜悯的蛮族形象,是去意指他对于法兰克人以及其他横渡莱茵河的日耳曼人的胜利,这一胜利于公元310年发表在特里尔(Trier)的颂词中得到庆祝。如下的摘录很好地表达了该演说的这个主题:[[67]]
11(1)因此,这就是我们现在正享受着的和平。因为我们现在并非是受到莱茵河波涌水流的保护,而是由于你的威名所带来的恐惧。即使让这一河流因夏日的灼热而干涸或者让它因为寒冷而冻结,敌人也不敢趁机跨越……(3)法兰克人知道他们能跨越莱茵河,并且你们将自由地接纳他们直至其死去,但是他们既不能希望胜利也不能渴求宽恕。 12(1)虽然如此,蛮族人的邪恶力量可能以任一种方式破除,并且因此敌军不应仅仅为他们的国王遭受的惩罚而悲痛,除此之外,战无不胜的皇帝,你们已经在布鲁克特利(Bructeri)赢取了一场毁灭性的袭击。……(3)因此,不计其数的人被屠杀,大量的人被俘。牲畜或被扣押或被杀戮,所有村庄皆被付之一炬;成年男子被捕捉,他们的不可靠使得他们不宜用于军事目的,而他们的残暴使得他们不宜被役使,只能被送到露天圆形剧场去接受惩罚,并且他们庞大的数目使得怒不可遏的野兽也筋疲力尽。这依赖于一个人的英勇和好运气,皇帝;这不是通过宽恕仇敌来购买和平,而是通过煽动他来赢得胜利。
拉丁颂词中的修辞夸张在这里可见一斑。我们可以确定并非所有的捕获者都被疲劳过度的野兽所猎杀。有些可能已进入军事服役,尽管演说者竭力地否认,这正如几个世纪以来发生在此前皇帝那里一样。一些人必定是以奴役而告终。只是在皇帝以及西部首都受到邀请的听众面前,陈列这些并不符合颂词的直接目的。君士坦丁凯旋门上的形象,被选来去展现皇帝作为征服者和蛮族仇敌的奴役者、通过战争中胜利去创建和平这一非常传统和理想化的形象(插图16)。图拉真、哈德良以及安东尼时期材料的再使用表明,公元4世纪早期的罗马人依然倾向于如他们的祖先一样的方式去展望他们的帝国,即使是现实状况有时已经相当不同。[[68]] 前述讨论已经强调了在将奴役的图像作为战争的后果方面,罗马的纪念艺术不同于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希腊艺术的限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罗马文化在类型以及很多图像的式样方面,深受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希腊的影响。当我们审视罗马战争图像中的奴隶制时,很多图像强烈地表明它们与古代近东的帝国存在文化上的一致。对一些比较样例的简要讨论将表明,罗马人在他们的主题选择方面将被认为是典型的或者是不起眼的。从埃及到古代近东庆祝战争中胜利的纪念性浮雕雕刻,经常刻画被赶去处死、奴役,或者驱逐出境的捕获者。早至公元前3千纪中期,在一系列的纪念性物体上,如所谓的“乌尔军标(Standard of Ur)”已经存在被缚战俘的形象。它来自阿卡德和拉格什(Akkad and Lagash)的石柱状纪念性建筑(Stone stelae),或者是来自于萨尔普勒(Sar-I Pul)的安努贝尼尼雕刻(Annubanini relief)。 [[69]]也应该提及埃及的例子,例如在努比亚拜特埃尔瓦利拉美西斯二世神庙(Ramesses Ⅱ’s temple at Beit el-Wali in Nubia)中的浮雕,或者是著名的哈布城浮雕(Medinet Habu reliefs),刻画的是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Ⅲ)打败利比亚人和公元前1174年海上民族的入侵,其中的很多人被捆绑着带走。[[70]]这些战俘的地位和预定命运并不总是易于确定,但是纪念公元前9至7世纪亚述国王所进行战争的浮雕雕刻,能够与铭刻、基础文本以及编年著作中记载这些战争的很多细节相对应。[[71]]文本和图像的这种结合使得我们注意到,亚述国王相当关注他们的胜利战争所带来的收益和影响。亚述战争图景的不断重复的主题提到所获战利品或贡物的数量和种类、敌军被杀死的人数和类型,以及他们所奴役的各类人群或者是强制他们去亚述帝国的其它部分去定居。根据雕刻以及它们相伴随的铭刻,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由抄书吏细心记述的。绝大多数的雕刻都在亚述城市里得到展示,在主神的神庙前,或者是由亚述统治者所建造宫殿中公共房间的墙上。就两者的公共背景和内容而言,他们大体类似于前述的罗马素材。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地的是颂扬亚述国王以及他的军队的权威,这既是面向国内参观者也是针对外族观光者。 在亚述的战争图景中,奴役非战斗人员的绝好例证体现在尼姆鲁德(Nimrud)西北宫殿的浮雕雕刻带上(插图17)。[[72]]它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65年,当时正值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Ⅱ,公元884年至859年在位)统治时期,它表现了阿淑尔那西尔帕的军队占领了一个城镇。在浮雕带的下方,牛群、妇女以及儿童正在被亚述士兵带走,与此同时,抄书吏记录着战利品的详情。他们的绝望透过妇女的姿态得到生动体现。 一块雕刻带最初展现在尼姆鲁德的中部宫殿,并可追溯至提革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pileser Ⅲ)统治时期(公元前745年至727年在位),展示的是占领阿斯塔图城(the city of Astartu)时获胜的国王在乘坐双轮战车,在国王头部上方的铭刻中对此有所叙述。这个城市的人口以及他们的牲畜,正在武装人员的监守下被带走(插图18)。这一场景对于亚述国王的持久吸引力通过这一事实得到展现,即它在国王以撒哈顿统治时期(king Esarhaddon, 公元前681年至前669年在位)作为尼姆鲁德西南宫殿装饰的一部分再次被使用。[[73]] 后者的父亲,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5年至前681年在位),目前现存的亚述艺术中关于这一主题的最为精致范例要归功于他,也就是奴役陷落之城拉基什(Lachish)居民的行进被详细地刻画在他在尼尼微的西南宫殿中一房间的墙上(插图19)。[[74]] 古代世界文化和政治的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直接寄予他们在战争中胜利的广度。胜利表明他们是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有能力保护那些承认他们统治的人,为他们带来以战利品、奴隶以及领土等为形式的物质利益,以及威望和地位等难以触摸得到但却并非不重要的回报。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也是表明他们的权威是神授并得到神助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很明显的是,早期近东王国、埃及人、亚述人以及罗马人,存在很多文化、社会以及政治差异,但是在这一点上大体相似。亚述国王和罗马皇帝的权威尤其高度依赖神性约束军事君主思想的支持,而军事君主将获取领土、战利品以及奴隶作为成功的主要尺度。 [[75]]用于纪念帝国军事成就的大型纪念物上战俘和奴役的生动描述表明,战争是奴隶的主要来源,而奴役战败者是罗马帝国战争的主要目的,在公共语境下予以庆祝和纪念将维持和增强这一思想意识。 [[76]] 当然,不过度强调帝国时代罗马纪念艺术中一些独特的要素是非常重要的。罗马战争图景中战斗的荣耀和立即消灭敌军将士,如同征服民众的奴役和剥削的长期影响,是同等重要的。捕获者的占有和处理可能不是罗马帝国时期战争图像的最重要主题,但它相当频繁地出现,并且这种频繁与罗马强调奴役俘虏是战争的目的之一是相一致的,这也被历史文本和记载所证实。 在自奥古斯都统治以来皇帝及其家族享有罗马胜利游行特权的背景之下,这一主题更为突出。该主题在帝国时代战争图景中出现,及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受到持续的欢迎,有助于强调罗马文化中皇帝与奴役之间的基本联系。罗马皇帝作为通过战争而成为奴隶的提供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得到颂扬。皇帝是大奴隶主,在法律领域是最终的监管者,并且通过资助大斗兽场以及其他圆形剧场的残杀游戏,他们还要对惩罚不守规矩的奴隶负责。 这一主要的图景特征,在罗马以外,尤其是在东部行省,也有体现,尽管在程度上不那么突出。甚至是在科林斯这样的希腊文化的伟大古代中心,征服敌军也被刻画在公共纪念物上,尽管它们的展现方式可能反映了调和道德、文化观念与政治屈服要求的需要,但却是艺术性占据主流的文化。在前述所谈及的纪念物上,所描述的对蛮族人的征服和奴役存在显而易见的明显趋势,绝大多数都是高卢人、日耳曼人或者是东方居民。这似乎意味着,假如奴役的敌军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这是极好的,意即不是希腊人或罗马人,而是蛮族人。在这里,需要强调的关键问题是,这并不是一个实际操作,而更多的是感知和明确表达的区别,它们根据特定社会的普遍道德风气而有所不同。似乎是,在帝国的某些区域,有意不采用将捕获者刻画为屈辱、脆弱奴隶的选择是可行的,而这种选择在罗马及其他地区通常也是被允许的。 奴役决不是征服的人口用来服务罗马帝国的唯一方式。我们可以设想有一系列的处置战俘的方式,这取决于他们失败时的情况以及相关条款。处死和和平地融合分处这一系列处置方式的两端。迁徙到别处和征召至罗马军队是罗马征服者对待他们前敌人的普遍方式,而他们在古代亚述和其他近东帝国也是典型的。 罗马艺术的资助者,特别是皇帝,要求他们的艺术者采用基本的形式、式样、场景以及风格创新,以便形成独特的公私艺术的罗马类型,庆祝征服的细节和对战败者的奴役,满足他们以及观众的期望。纪念建筑的内容和其他艺术项目表现了资助者提升帝国主题,为达到此目的,艺术者以多种方式调整图案和主题,对他们的创新展现了很少的疑虑,如果有的话。在前述所探讨的样例中,对支配和奴役的庆祝几乎是热情洋溢的,这表明他们承认并予以接受,可能甚至是欢迎的,犹如是罗马帝国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权力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你让人去行使它,这是不言而喻的。帝国时期的罗马纪念艺术表现的战争中征服和奴役的图景,表明了罗马人在对他们所打败的敌军行使他们的权利时是多么的怡然自得。[77]
译者简介:贾文言,1981-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枣庄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世界古代史; 王坤霞,1991-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希腊化艺术。 [[1]] 布拉德利在《论元首制下的俘虏》(K. Bradley, ‘On captives under the Principate’, Phoenix 58 [2004]: 298-318.)中探讨了罗马帝国艺术中频繁而醒目出现的囚犯,并特意提到元首制时期常规奴隶供应的维持问题。布拉德利明确将其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将战败敌方人格化为俘虏以及在纪实艺术形式中反复择取男性、女性和儿童作为战囚展现的适宜形象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俘获男性、女性和孩童是频繁战斗、胜利和战争的常态和可核实成果。”(第303-04页) [[2]] 关于罗马人对希腊化战争场面传统的接受和采纳,参见T. 赫尔舍,《罗马艺术中的图像语言》,A.斯诺德格拉斯和A.金茨尔-斯诺德格拉斯译(T. H?lscher, The language of images in Roman art, trans. A. Snodgrass and A. Künzl-Snodgrass, Cambridge, 2004, p.23-46.)。 [[3]] 赫尔舍,《罗马艺术中的图像语言》(H?lscher, The language of images in Roman art (n. 2 above) 41.)。也可参见 T. 赫尔舍,《罗马人的胜利:罗马胜利女神从诞生到公元3世纪的历史和特征考古调查》(T. H?lscher, Victoria Romana. Arc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und Wesenart der r?mischen Siegesg?ttin von den Anf?ngen bis zum Ende des 3. Jhr. N. Chr.,Mainz, 1967.);《国家纪念碑与公众:罗马从共和国的沉沦到帝国的巩固》,康斯坦斯古代史讲座与研究,第九期,康斯坦斯,1984年(Staatsdenkmal und Publikum. Vom Untergang der Republik bis zur Festigung des Kaisertums in Rom. XENIA Konstanzer Althistorische Vortr?ge und Forschungen , Heft 9 [Konstanz 1984])。 [[4]] 涅瑞伊得纪念碑可追溯至公元前400年,很可能是吕西亚王朝一个名为阿尔比那斯(Arbinas)的墓碑。它采用了一种传统吕西亚石碑墓的希腊化形式,但其浮雕所刻内容似乎受到近东纪念碑的影响,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阿契美尼德皇家浮雕;参见M.C. 鲁特,“阿契美尼德艺术中的国王和王权:帝国肖像研究的兴起”,载《伊朗研究》(M. C. Root, The king and kingship in Achaemenid art: essays on the creation of an iconography of empire [Acta Iranica 19, Leiden 1979] 280-81.)。彩陶上所绘的缚囚例证见于贡比涅的穆赛安托万博物馆(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黑绘装饰瓶,编号124)和雷丁的乌尔博物馆(公元前四世纪阿普利亚红绘双耳喷口杯,编号1935.87.34) [[5]] 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战俘命运的详细分析,参见A. 帕纳戈普洛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俘虏和人质》,(A. Panagopoulos, Captives and hostage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 Athens,1978.)。对公元前360年以后的群体奴役的调查,参见H. 沃尔克曼,《希腊化-罗马时期被征服城市居民的集体奴役》(H. Volkmann, Die Massenversklavungen der Einwohner eroberter St?dte in der hellenistisch-r?mischen Zeit, Wiesbaden 1961, 2nd ed. Stuttgart, 1990, p.14-71.) [[6]] 参见 P. 迪克雷,《从起源到罗马征服的古希腊战俘处理》(P. Ducrey, Le traitemen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dans la Grèce antique des origins à la conquête romaine, 2nd ed, Paris, 1999, p.107-47.);Y. 加朗,《古希腊奴隶制》,J.劳埃德译(Y. Garlan, 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 trans. J. Lloyd, Ithaca and London, 1988, p.32-34, 45-53.)。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古典时期公元前427年,漫长而痛苦的普拉提亚围攻之后的集体奴役(修昔底德, 3.68)。更多例证参见W.K.普里切特,《战时希腊城邦》(第五部分)(W. K. Pritchett, The Greek state at war. Part V,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1991, p.226-34.);A. 查尼奥提斯,《希腊化世界的战争:一部社会和文化史》(A. Chaniotis, War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2005, p.125, 142.)。 [[7]] 色诺芬,《阿格西劳传》,7.6(Xen. Ages. 7.6.). [[8]] 普鲁塔克,《阿格西劳传》,7(Plut. Ages. 7).蛮族人就该做奴隶,而被奴役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野蛮的”的文化自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6)中得到充分阐述。关于讨论,参见加朗,《古希腊奴隶制》,第120-126页;P.加恩西,《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时期的奴隶制观念》(P. Garnsey, Ideas of slavery from Aristotle to Augustine, Cambridge, 1996, p.76-78.)。 [[9]] 关于主要例证的表现和分析,参见 J.J. 波利特,《希腊化时期的艺术》(J. J. Pollitt, Art in the Hellenistic age , Cambridge, 1986, p.79-97.);R.R.R. 史密斯,《希腊雕塑》(R. R. R. Smith, Hellenistic sculpture, London, 1991, p.99-104.);J.R.马泽尔,“帕加马阿塔路斯一世的胜利纪念碑”,见R.F.道科特和E.M.默尔曼合编《第十五届古典考古学国际会议论文集》(J. R. Marszal, ‘The victory monuments of Attalos I at Pergamon’, in R. F. Docter and E. M. Moorman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X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lassical archaeology, Amsterdam, July 12-17, 1998 [Amsterdam 1999]: 251-53)。关于卡皮托利亚所藏“垂死的高卢人”与路德维希群雕,参见 I.M. 费里斯,《罗马之敌:罗马人眼中的蛮族人》(I. M. Ferris, Enemies of Rome: barbarians through Roman eyes , London, 2000, p.6-12.);M.比尔德和J.亨德逊,《古典艺术:从希腊到罗马》(M. Beard and J. Henderson, Classical art: from Greece to Rome, Oxford and New York, 2001, p.160-64.)。M. 马文,“路德维希‘蛮族人’大艺术中的历史”,见E. 加兹达编《古代仿真艺术:从当代到古典古代的原创与传统》(M. Marvin, ‘The Ludovisi barbarians: history in the grand manner’, in E. Gazda (ed.), The ancient art of emulation: studies in originality and tradition from the present to classical antiquity.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Supplementary Volume I [Ann Arbor 2002]: 205-23)认为它们并非希腊化原作的复制品,而是公元2世纪基于图拉真和马尔库斯·奥里略纪功柱上相似主题和样式的雕带创作。 [[10]] 费里斯,《罗马之敌》,第8页;也可参阅波利特,《希腊化时代的艺术》,第86-88页。 [[11]] 特别注意普林尼对一个吹号手雕像的评论,它由帕加马的雕像家埃皮格努斯所创作。(普林尼,《自然史》,34.88)(Plin. HN 34.88) [[12]]关于罗马征服意大利期间的奴役,参见沃尔克曼,《希腊化-罗马时期被征服城市居民的集体奴役》;W.V. 哈里斯,《罗马共和国(公元前327-70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W. V. Harris, 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 Oxford, 1979, p.59.)。 [[13]] 参见 J.W.里奇,“条约、结盟和罗马征服意大利”,见P.德.苏萨和J.弗朗斯编《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J. W. Rich, ‘Treaties, allies and the Roman conquest of Italy’, in P. de Souza and J. France (eds.), War and peace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 [Cambridge 2008]: 51-75, 62-65.);K.霍尔克斯卡姆普,“忠诚,对忠诚的屈从,借贷和分配的誓约:罗马的法权、宗教和仪式”,见C.布鲁恩编《罗马共和国中期(约公元前400-133年):政治、宗教和史学史》(K. H?lkeskamp, ‘Fides – deditio in fidem – dextra data et accepta: Recht, Religion und Ritual in Rom’, in C. Bruun (ed.), The Roman Middle Republic: politics, religion and historiography c. 400-133 B.C. Acta Instituti Finlandiae 23 [Rome 2000]: 223-50);“征伐、竞争和共识:罗马在意大利的扩张和贵族阶层的兴起”,载《历史》(‘Conquest, competition and consensus: Roman expansion in Italy and the rise of the nobilitas’, Historia 42 [1993]: 12-39);W.达尔海姆,《罗马法的结构与发展》(W. Dahlheim, Struktur und Entwicklung des r?mischen V?lkerrechts, Munich, 1968, p.5-109.)。 [[14]] 参见 A.M.艾克斯泰恩,《波利比乌斯<通史>中的道德观》(See A. M. Eckstein, Moral vision in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95, p.194-236.)。通常可参见《地中海无序政治、邦际战争和罗马的兴起》(Eckstein, 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 2006.) [[15]] 对希腊战争赎金的案例考察,参见普里切特,《战时希腊城邦》,第245-283页。 [[16]] 波利比乌斯,9.42.5-8.(佩顿译)(Polyb. 9.42.5-8 [trans. Paton].) [[17]] 波利比乌斯,22.8.9-10;参见 F.W. 沃尔班克,《波利比乌斯历史注疏》(三卷本)(F. W. Walbank,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3 vols., Oxford, 1957-79, vol. I, 186 and vol. III, 189-90.) [[19]] 关于演说的真实性和演说者身份,可参见 H.U.维默尔,《希腊化史学史中的罗德斯传统》(H.-U. Wiemer, Rhodische Traditionen in der hellenistischen Historiographie, Frankfurt, 2001, p.49-58.);沃尔班克,《波利比乌斯历史注疏》,卷二,第274-275页。 [[20]] 参见哈里斯,《战争与帝国主义》;J.W.里奇,“恐慌、贪婪和荣耀:罗马共和国中期战乱起因”见J.里奇和G.希普利合编《罗马世界的战争与社会》(J. W. Rich, ‘Fear, greed and glory: the causes of Roman war-making in the Middle Republic’, in J. Rich and G. Shipley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93]: 38-68.);T.J.康奈尔,“罗马帝国扩张的尾声”见J.里奇和G.希普利合编,《罗马世界的战争与社会》),第139-170页;B. 坎贝尔,《罗马帝国(公元前31年-公元284年)的战争与社会》(B. Campbell, War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ome 31 BC-AD 284,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p.1-21.)。 [[21]] 按地区组织的研究,参见沃尔克曼,《希腊化-罗马时期被征服城市居民的集体奴役》。 [[23]] 鲍桑尼阿斯,7.16.8;欧罗西乌斯,4.23.3.(Paus. 7.16.8; Orosius 4.23.3.) [[24]] 将奴隶获取作为罗马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参见哈里斯,《战争与帝国主义》,第80-86页;N.K.劳,《罗马世界的商人、水手和海盗》(N. K. Rauh, Merchants, sailors and pirates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 , 2003, p.29-44.);布拉德利,《元首制下的俘虏》。 [[25]] 例如,希罗多德,7.135;埃斯库罗斯,《波斯人》,24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7b,1328b-1329a. 对这些及其他文本的探讨参见加朗,《古希腊奴隶制》,第120-126页;加恩西,《奴隶制观念》,第35-38页。 [[26]] 修昔底德,1.139,144. 关于某些希腊战争带有更明显帝国主义色彩,将政治自由作为公开目标,参见R.西格和C.塔普林,“亚洲的希腊人:一种概念的来源和口号的诞生”,载《希腊研究》(R. Seager and C. Tuplin, ‘The Greeks of Asia: on the origins of a concept and the creation of a slogan’, JHS 100 [1980]: 141-54.);R.西格,“亚洲希腊人的自由:从亚历山大到安提柯”,载《古典学季刊》(R. Seager, ‘The freedom of the Greeks of Asia: from Alexander to Antiochus’, CQ 31 [1981]: 106-12.)。 [[27]] 关于凯旋式的起源,参见H.S.韦斯内尔,《凯旋式:对罗马凯旋式的起源、发展和意义的探究》(H. S. Versnel, Triumphus: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meaning of the Roman triumph, Leiden, 1970.)。其观点被J.鲁普克所反对,J.鲁普克,“凯旋者和祖先仪式:在象征人类学与巫术之间”,载《守护神》(J. Rüpke, ‘Triumphator and ancestor rituals: between symbolic anthropology and magic’, Numen 53 [2006]: 251-89),但得到韦斯内尔的拥护(韦斯内尔,“红色(鲱鱼?)关于凯旋式起源的新理论批判”,载《守护神》)(Versnel, ‘Red (herring?). Comments on a new theo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triumph’, Numen 53 [2006]: 290-326.);凯旋队列的一般性介绍见E. 孔茨尔,《罗马凯旋式:古代罗马的胜利庆典》(E. Künzl, Der r?mische Triumph: Siegesfeiern im antiken Rom, Munich, 1988.);T. 伊特根豪斯特,“万人空巷:罗马共和国的凯旋式”,载《备忘》(T. Itgenhorst, Tota illa pompa. Der Triumph in der r?mischen Republik, Hypomnemata 161 [G?ttingen 2005]);M. 比尔德,《罗马凯旋式》(M. Beard, The Roman triumph, Cambridge MA, 2007)。 [[28]] 普鲁塔克,《埃利乌斯》,32-34.(Plut. Aem. 32-34.) [[29]] 狄奥·卡西乌斯,43.19.4.(Dio Cass. 43.19.4.) [[30]] 约瑟夫,《犹太战记》,7.155.(Joseph. BJ 7.155.) [[31]] 参见弗罗鲁斯,《罗马史纲要》,1.38.(See Florus Epit. 1.38.) [[32]] 罗马凯旋式上被游行示众的俘虏,参见波利比乌斯,2.31.5-6(公元前225年);李维,34.52.4-12(公元前194年);狄奥多鲁斯,31.8.12(公元前167年);阿庇安,《西班牙战争》,98(公元前132年);狄奥·卡西乌斯,51.21.8(公元前29年);塔西佗,《编年史》2.41,斯特拉波,7.1.4(公元17年);约瑟夫,《犹太战记》,7.123-157(公元71年)。文学摹写参见奥维德,《爱情三论》,1.219-252.。很难证实凯旋式上出现的俘虏数目,尤其文学描写集中在众人之狂欢和战利品之盛(其中的许多或由俘虏带来?);参见布拉德利,《元首制下的俘虏》,第302页;比尔德,《罗马凯旋式》,第118-119页。 [[33]] 例如,约瑟夫,《犹太战记》,6.412-418。《庆典》428-430行将一句流行的罗马谚语“待售的撒丁人”,归结为公元前176年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胜利之后的撒丁战俘的大肆贩卖。 [[34]] P.J.霍利迪,《视觉艺术中的罗马历史庆典起源》(P. J. Holliday, The origins of Roman historical commemoration in the visual arts, Cambridge, 2002, p.30-62, 63-121.)。 [[35]] 参见 P. 赞克,《奥古斯都时代的图像影响》,A. 夏皮罗译(P. Zan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trans. A. Shapiro, Ann Arbor, 1988, p.68-70.);D.E.E.克莱纳,《罗马雕像》(D. E. E. Kleiner, Roman sculp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2, p.85-86.);费里斯,《罗马之敌》,第33-34页。 [[36]] 参见费里斯,《罗马之敌》,第40-44页。更长的名单参见布拉德利,《元首制下的俘虏》,第298-301页。 [[37]] 参见赞克,《奥古斯都时代的图像影响》,第230-235页。另一玉石浮雕,即知名的“法兰西大浮雕玉石”,霍克追溯至提比略在位期间。它具备类似特征,但以更体面一些的方式刻画俘虏;参见比尔德和亨德逊,《古典艺术》,第196-197页。 [[38]] 这些人物形象在奥古斯都艺术中的重要性,参见赞克,《奥古斯都时代的图像影响》,第172-192页。 [[39]] 奥古斯都及继任皇帝们通过战争中的胜利,为人们带来了和平和繁荣,他们所宣扬的这种思想参见P.德. 苏萨,“赢得和平:罗马皇帝,和平缔造者”,见P.德.苏萨和J.法兰西合编《古代和中世纪史上的战争与和平》(P. de Souza, ‘Parta victoriis pax: Roman emperors as peacemakers’, in P. de Souza and J. France (eds.), War and peace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2008, p.76-106.)。 [[40]] 探讨和详细书目,参见E.W. 利奇,《古罗马和那不勒斯湾绘画中的社会生活》(E. W. Leach, The social life of painting in ancient Rome and on the Bay of Naples, Cambridge, 2004,p.137-42.)。 [[41]] “以拍卖方式出售”(sub hasta venditis )见李维,23.38.7,一般的“充公征用”(ius hastae )见塔西佗,《编年史》,13.28.将长矛同木棍、权杖等同起来,参见盖乌斯,《法学阶梯》,4.16,“人们利用木棒替代长矛,作为正当所有权的象征。”(festuca uti quasi hastae loco, signii quodam justii domini.) [[43]] 留意奥古斯都时期作为战利品的雕带,现在都灵和博洛尼亚。(费里斯,《罗马之敌》,第34页)。 [[44]] 弗拉维时期的凯旋式,参见约瑟夫,《犹太战记》,7.3-7;孔茨尔,《罗马凯旋式》,第9-19页;比尔德,《罗马凯旋式》,第43-45,93-101页。 [[45]] 图像损坏导致我们无法清晰辨认,我认为这一雕刻带的人物既包含搬运工又有俘虏(可能两种角色由同类人担任)。 [[47]] 参见J.B. 坎贝尔,“谁是“军功阶层”(viri militares )?”,载《罗马研究》(J. B. Campbell, ‘Who were the ‘viri militares’?’, JRS 65, [1975]: 11-31.);德·苏萨,《赢得和平:罗马皇帝,和平缔造者》。 [[48]] 两物件皆是属大英博物馆的希腊和罗马藏品(塞浦路斯陶灯 GR 18681-10.658;埃及雕像 GR 19837-23.1) [[50]] 关于复原,可参见Y.勒.伯恩克,《罗马帝国军队》(Y. Le Bohec, The imperial Roman army, London, 1994; translation of L’Armée Romaine sous le Haut-Empire, Paris 1989, pl. XXII.)。一般介绍参见F.A. 莱珀和S.弗里尔,《图拉真纪功柱》(F. A. Lepper and S. Frere, Trajan’s column ,Gloucester, 1988.)。 [[51]] 关于阿达姆克利西纪念碑,参见I.A.里士满,“阿达姆克利西”,载《罗马英国学院论文》(I. A. Richmond, ‘Adamklissi’,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35 [1967]: 29–39);安德里安·冯·拉杜勒斯古,《阿达姆克利西胜利纪念碑》(Adrian V. R?dulescu, Das Siegesdenkmal von Adamklissi, Konstanza , 1972.);L.罗西,《阿达姆克利西柱间壁合图拉真纪功柱雕刻带概览:再谈真实和幻想》,载《学会》(L. Rossi, ‘A synoptic outlook of Adamklissi metopes and Trajan’s column frieze. Factual and fanciful topics revisited’, Athenaeum 85 [1997]: 471-86.);费里斯,《罗马之敌》。 [[52]] 马尔库斯·奥里略纪功柱参见 I.M. 费里斯,《仇恨与战争:马尔库斯·奥里略纪功柱》(I. M. Ferris, Hate and war: the column of Marcus Aurelius, Stroud, 2009.);C.R. 惠特克,《罗马及其疆界:帝国的动态发展》(C. R. Whittaker, Rome and its frontiers: the dynamics of empire,London, 2004, p.120-22.)引用了来自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的塞巴斯泰昂(Sebasteion)神庙雕刻带之一,展现了阳刚的克劳狄乌斯败于大不列颠女性化形象之下的画面,参见R.R.R. 史密斯,“阿弗罗狄西亚的塞巴斯泰昂浮雕”,载《罗马研究》(R. R. R. Smith, ‘The imperial reliefs from the Sebasteion at Aphrodisias’, JRS 77 [1987]: 88-138.)。罗马艺术中的这一主题可参见S. 狄龙,《图拉真和马尔库斯·奥里略纪念柱上的女性与罗马大胜的视觉语言》,见S.狄龙和K. 韦尔奇合编,《古罗马的战争表现》(S. Dillon, ‘Women on the columns of Trajan and Marcus Aurelius and the visual language of Roman victory’, in S. Dillon and K. Welch (eds.), Representations of war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 2006]: 244-71);讨论参见费里斯,《罗马之敌》,第162-168页;《仇恨与战争》,第111-130页。 [[53]]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30.(Tac. Agr. 30.)这一时期罗马人对帝国主义态度的模棱两可,参见德·苏萨,《赢得和平:罗马皇帝,和平缔造者》和G. 伍尔夫,《罗马和平》,载《古罗马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第171-194页。 [[54]] 《拉丁铭文选》415号,即《拉丁铭文集成》卷六,第1033号(ILS 425 = CIL 6.1033.)。塞维鲁凯旋门的基础性著作,参见R.布里连特,《罗马广场上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凯旋门》,载《罗马美国学会》(R. Brilliant, ‘The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in the Roman Forum’,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29 [1967].) [[55]] 奥古斯都的帕提亚凯旋门,参见赞克,《图像影响》,第186-192页。 [[56]] A.库利,《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奥古斯都皇帝》,见S.斯温、S.哈里逊和J.埃尔斯纳合编《塞维鲁文化》,第395页(A. Cooley, ‘Septimius Severus: the Augustan emperor’, in S. Swain, S. Harrison, and J. Elsner (eds), Severan culture, Cambridge, 2007, p.385-97.);C.B.罗斯,《奥古斯都时期罗马的帕提亚人》,载《美国考古》 (C. B. Rose, The Parthians in Augustan Rome’, AJA 109 [2005]: 21-75.) [[57]] 对君士坦丁凯旋门上被再次利用的存世雕刻带的解读,参见J.S.赖伯格,《马尔库斯·奥里略雕刻带浮雕》(J. S. Ryberg, The panel reliefs of Marcus Aurelius, New York, 1967)。 [[58]] 关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帕提亚远征,参见 A.R. 博利,《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非洲的皇帝》(A. R. Birley, Septimius Severus: the African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1971, 1988.)。泰西封于公元197年后期被袭并劫掠一空,但两次哈特拉之围失败。 [[59]] Z.纽比,《转折中的艺术?塞维鲁艺术中的主题与风格》,见《塞维鲁文化》,第222页(Z. Newby, ‘Art at the crossroads? Themes and style in Severan art’, in Swain, Harrison, and Elsner (eds.), Severan Culture (n. 56 above) 201-49, at 222.)。 [[60]] 费里斯将它们解读为“普通的凯旋式场景”,费里斯,《罗马之敌》,第122-124页。 [[61]] 这些雕刻可能是在纪念碑正面树立后数十年后才增置的。 [[62]] 参见史密斯,《阿弗罗狄西亚斯的塞巴斯泰昂浮雕》;费里斯,《罗马之敌》,第124页;布拉德利,《元首制下的俘虏》,第313-314页。 [[63]] 参见 C.C.维穆勒,《希腊和小亚的罗马帝国艺术》(C. C. Vermeule, Roman imperial art in Greece and Asia Minor, Cambridge MA, 1968.);克莱纳,《罗马雕像》,第209-212页。 [[65]] 关于君士坦丁凯旋门,参见 L. 阿邦丹扎,《罗马角斗场山谷》(L. Abbondanza, The valley of the Colosseum ,Rome, 1997, p.32-47.);J. 埃尔斯纳,《帝国时期的罗马和基督教的胜利》(J. Elsner, Imperial Rome and Christian triumph, Oxford, 1998,p.78-82, 187-89.);费里斯,《罗马之敌》,第131-135页。“劫掠”主题的重复运用之议,参见 E. 梅尔,《罗马仍存,帝王何在:从戴克里先到狄奥多西二世,分权帝国的皇家艺术研究》(E. Mayer, Rom ist dort, wo der Kaiser ist. Untersuchungen zu den Staatsdenkm?lern des dezentralisierten Reiches von Diocletian bis zu Theodosius II, Mainz, 2002, p.185-202.);H. 普鲁克纳,《君士坦丁皇帝后的图像:战利品的展现》,载《忒提斯》(H. Prückner, ‘Kaiser Konstantins Bilderbogen oder: Die Botschaft der Spolien’, Thetis 15 [2008]: 59-75) [[67]] 《拉丁语颂词集》,6.11-12.尼克松译,转自C.E.V.尼克松和B.S.罗杰斯,《晚期罗马皇帝赞歌:拉丁语颂词集》(Pan. Lat. VI.11-12; translations by Nixon from C. E. V. Nixon and B. S. Rodgers, In praise of later Roman emperors: the Panegyrici Latin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4, p.211-53.)。 [[68]] 关于选取较久远材料所含的意义的进一步讨论,参见费里斯,《罗马之敌》,第134-135页;梅尔,《罗马仍存,帝王何在:从戴克里先到狄奥多西二世,分权帝国的皇家艺术分析》,第195-202页。加列利乌斯在首都特萨洛尼基建(约公元300年)的凯旋门上有帝国胜利和波斯敌人屈服的场景,参见艾尔斯纳,《帝国时期的罗马和基督教的胜利》,第129-130页。帝国时期的艺术文学中的北部蛮族描述详见C.海茨,《善、恶、丑:罗马艺术形象中的北部蛮族人》(C. Heitz, Die Guten, die B?sen und die H?sslichen. – N?rdliche ?Barbaren’ in der r?mischen Bildkunst, Hamburg, 2009, p.27-250.)。 [[69]] 参见P.德. 苏萨编,《战时古代世界:一部全球史》(P. de Souza (ed.), The ancient world at war: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2008, p.46-50.);萨尔普勒浮雕见鲁特,《阿契美尼德艺术中的国王和王权》,第196-200页,插图49。 [[70]] 参见鲁特,《阿契美尼德艺术中的国王和王权》,第220,245-246页,插图51b(拜特瓦利);德·苏萨编,《战时古代世界》,第44-45页(哈布城)。关于埃及战争参见I.肖和D. 博特赖特,《古埃及战事》,见德·苏萨编,《战时古代世界》,第28-45页。 [[71]] 亚述战争和帝国主义见 N. 塔利斯,《古代近东战争》,见德·苏萨编,《战时古代世界》,第55-65页。亚述雕像参见J.里德,《亚述雕像》(J. Reade, Assyrian sculpture, London, 1983, 1998.) [[72]] 阿淑尔纳西尔帕及其王宫见里德,《亚述雕像》,第34-41页。 [[74]] 拉基什的陷落(公元前701年)和辛那赫里布塑像见里德,《亚述雕像》,第65-71页。 [[75]] 早期希腊化君主也运用过类似思想。见注14中的作品,以及德·苏萨,《赢得和平:罗马皇帝,和平缔造者》和《战时古代世界》,第2-12章。二者之间可能有直接联系。尽管从埃及到亚述又及罗马的某一特定主题难以追溯,但帝国时期的艺术家与赞助人可能目睹过上文讨论过的物品。就学者们不遗余力以近东视域去研究古希腊和罗马的帝国历史,参见J.维施霍费尔,“古代世界和近东史:通史的申辩”,载《亚美尼亚、希腊人和罗马人》(J. Wieseh?fer, ‘Histoire de l’antiquité et Orient ancient, ou: plaidoyer pour une histoire universelle’, in Iraniens, Grecs et Romains, Studia Iranica 32 [Paris 2005]: 27-51) [[76]] 参见布拉德利,《元首制下的俘虏》,这些纪念碑可作为帝国时期战争中的奴役是奴隶来源的证据。 [77]本文的一稿已于2007年9月在麦克马斯特大学多哥萨蒙古典学术会议(Togo Salmon Classics conference at McMaster University)上做过报告。谨在此致谢与会人员的批评和建议,尤其是基斯·布拉德利(Keith Bradley)、维尔纳·埃克(Werner Eck)、米歇尔·乔治(Michele George)、桑德拉·乔希尔(Sandra Joshel)、娜塔利·坎彭(Natalie Kampen)以及诺埃尔·伦斯基(Noel Lenski)。我还要感谢两位匿名审阅人对论文的书写文本提出的帮助和建设性意见。第二稿于2010年11月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萨克索研究院(University of Copenhagen’s SAXO-Institute)做过展示。同样感谢文森特·加布里埃尔森(Vincent Gabrielsen)及其同事和学生的宝贵意见。我在都柏林大学的同事亚历山大·泰恩(Alexander Thein)博士在某些重要学术研究的方向上予以指引。若没有古典学研究所的主管与职员(Director and staff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以及希腊罗马协会联合图书馆(the Joint Library of the Hellenic and Roman Societies)所提供的便利设施与协助,以及伦敦瓦尔堡研究院(Warburg Institute in London)和都柏林大学詹姆斯·乔伊斯图书馆(the James Joyce Library at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的大力协助,本文将无法完成。一如既往地,最诚挚的谢意致以我的夫人,德布拉·德·苏萨博士(Dr Debra de Souza),她为本文提供了精美图片和深刻洞见。
|
 首页
首页